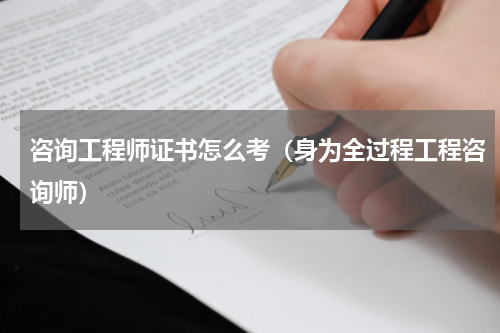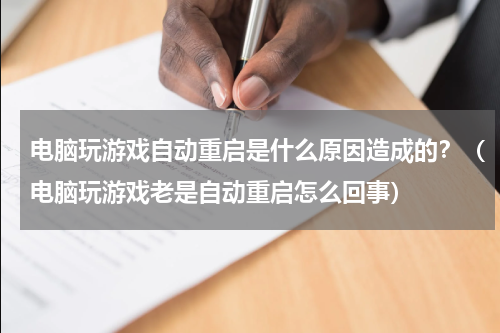如今城市的出生率在降低,死亡率却节节攀升。很明显的凶杀案。阿伟的声音从口罩后传来,他已经把骷髅装入了尸袋中。23点23分23秒,流浪汉的死亡时间。3今年年初,我全款在二环买了一套小三户,准备明年与希文结婚,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,当初心脏出了问题,她也没离开我。心脏移植手术很麻烦,需要从胸骨正中开胸,暴露纵隔,打开心包,切断大血管后通过体外循环机进行辅助循环。

作者:咖啡杯里的茶
1
我是清道夫,负责A城中某些特殊的清理工作。
这种职业月薪过万,拼的是胆量和过硬的八字属相,我做这份工作三年了,当初带我的老张已经退休,现在轮到我带新人。
大约你已经猜到了,我做的是与死人有关的工作,我们负责清理死亡现场。
人生不过两件大事,生与死。如今城市的出生率在降低,死亡率却节节攀升。我们忙得停不住脚,最多的一天清理了四个死亡现场,一闭上眼,那些流着尸水钻着虫子的尸体就在我眼前晃荡。
我们的工作绝对对得起那个高昂的薪水,因为你永远无法想象我们面对的是怎样骇人的现场。
馊臭的饭菜,老鼠蟑螂成灾,腐败的尸体,蜂拥而出的蛆虫……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不能善终的人类,最难打理的是凶案现场。
被砍得七零八落的尸块,溅在墙壁上的鲜血都要擦许久。
浴缸中泡烂了的女人,甚至无法把她完整地打捞起来,她肿得像一块泡烂了的面包,浑身都是虫子。
死了半个月无人发现的孤独老人,她的整张脸都被饥饿的猫扒来吃了,屋子中充满了诡异的味道,新人阿伟进入房间的一瞬间就呕吐了出来。
我盯着满桌的蟑螂,一脸平静地把浑身发软的阿伟扶到了屋外。
阿伟跟着我三个月了,明明八字是个命硬的人,却偏偏长了一张苍白的脸,我看得出每一次工作他都怕得瑟瑟发抖却强作镇定。
阿伟需要钱……做清道夫的谁他妈不需要钱,难道是因为热爱和死人打交道?我没有赶走阿伟,因为我招了足足两个月才找到这样一个助手。
哦,我的头儿老张是我亲自处理的。他用一条领带跪着自缢在了厕所的水管上,他的存折上有八十六万,却用一条八块六的领带自杀了。
2
阿伟在门口点了三根香,我们俩毕恭毕敬地拜了拜。死者为大,不管他是高官商贾还是街边流浪汉,永远不要和死者过不去,因为人人都要死。
这次我们处理的是浴缸中的一具骷髅,死者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,失意的穷光蛋,自杀在浴缸中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附近的居民说他是个流浪汉,许久不见他了,以前经常神经兮兮地坐在河边看书,没正经工作,就靠着收售破烂过日子,他收得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二手书。
流浪汉住的地方是河边的一个铁皮搭建的违章小屋子,这大概是我处理过最干净的死亡现场了,正因为它的干净让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
墙角一个烂书架上摆满了哲学、神学、宗教类的书籍,一丝不苟地按照类别摆放,甚至还做了颜色的归类。这是一个有强迫症的家伙,抽屉中的东西也摆放得整整齐齐,翻看他的毕业证,竟然是某名牌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。
我冷笑,一个读书读傻了的家伙。
“师父,好像不对劲。”阿伟戴着手套,蹲在浴缸边,指着那具骷髅架。
“废话,要你说。”我白了阿伟一眼,“别多事。”
人体从死亡到腐烂,最后烂到只剩一具骷髅,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,就算炎热的高温,排除昆虫啃噬等条件,仅仅自然腐烂的话,需要三个月。
但是今年的冬天冷得像个坟墓,尸体不可能坏得这么快,此时春天的气候依旧需要穿羽绒服。气温越低越干燥的环境,尸体腐烂得就越缓慢。自然骷髅化的骷髅颜色也与用药水处理过的完全不同,这具骷髅是被人活生生溶掉肌肉的。
很明显的凶杀案。
阿伟“哦”了一声,闭上双眼,握着脖子上开了光的玉观音,嘴里念念有词。
我白了他一眼,关上抽屉,到门口去抽烟,余光瞄到那三根香,两长一短,真够邪门的。而我手中的烟,在呼呼刮来的河风中,怎么也点不燃。
“师父……”阿伟的声音从口罩后传来,他已经把骷髅装入了尸袋中。
我走过去,看到浴缸中一块裂了纹的石英表,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,但我却鬼使神差地把它揣进了自己的怀中。
23点23分23秒,流浪汉的死亡时间。
我不信邪。
3
今年年初,我全款在二环买了一套小三户,准备明年与希文结婚,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,当初心脏出了问题,她也没离开我。这年头钱容易挣,真爱难找。
希文是妇幼院的护士,也是个胆大的女人,经常给我八卦手术室做人流的女人如过江之鲫,放大悲咒都放不过来,整个走廊都阴森森的。
“你怎么戴了块破表?”她突然盯着我手腕上的表。
“这叫遗憾美,你看那表面裂的蛛丝纹,是不是很有艺术感?”我凑过去亲她。
她脸上的疑惑表情一闪而过,但很快就拿出手机给我们俩拍合照。
“这款APP超有趣,可以通过照片测年龄,看,我显得好年轻,软件认为我只有二十岁!你二十八岁倒是蛮准的……”希文的声音越来越小,我凑过去看手机屏幕,发现我们的头顶上面都有一个小人和一个数字。
诡异的是,沙发后昏暗的窗帘处也有一个小人和一个数字。
二十八!
我和希文对视一眼,同时转过头去,空荡荡的沙发后,什么也没有。
入夜,我睡得特别沉,像死去了一样,突然觉得浑身冰凉,我猛地睁开双眼,赫然发现自己浑身赤裸地躺在装满冰块的浴缸中!
我挣扎着,想要坐起来,但是模糊的视线中什么也看不清,有人给我打了麻药!
“救……救命……”我想要喊叫,喉咙却只能发出沙哑的嘎嘎声。
“可以了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膜中,但是我却怎么也看不清楚那个人的模样,只觉得一把冰凉的手术刀刺入了我的胸口——
“啊!”我猛地从床上坐起,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是手腕上的表冰到了我的胸口,害我做了噩梦!
我飞快脱掉破表,却再也睡不着了,只能干瞪着眼盯着天花板发呆。
突然,一股刺鼻的液体从上面喷洒而下,我痛得连连惨叫,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融化成了一具惨白的骷髅。
“啊!”我一个激灵,睁开了双眼,拼命抚摸着自己的身体,还好,什么都还在。
我吓得冷汗直冒,心有余悸地摸着胸口的疤痕打了好几个冷颤。
三个月前,我做了一个心脏移植手术,我哥是医生,我也排了大半年的队,哥说如果我不是运气好,五年后也轮不到我。心脏移植需要一个漫长恢复期,我运气好,身体没有出现半点排斥现象。
心脏移植手术很麻烦,需要从胸骨正中开胸,暴露纵隔,打开心包,切断大血管后通过体外循环机进行辅助循环。供体的心脏在取出之前,给予氯化钾注射处理使心脏停搏,取出后放入冰中保存。
通常供体心脏可以在冰中保存4-6小时。
我想到了浴缸中的那些冰,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。
深夜新闻中正在报道警方查获了一批黑市器官贩子,用金钱引诱一些无知的年轻人或者急需用钱的人贩卖自己的器官,以肾脏居多,卖家只能拿到一两万,器官贩子却可以提成十来万,卖家像牲口一样被关在简陋的房间中……
“一些流浪汉也成为了黑市器官贩子的目标……”女主播在电视中正襟危坐。
我关上了电视,枯坐在沙发中,无意识地把玩着手腕上的石英表。
4
“你昨晚怎么半夜三更起来看电视?叫你也不答应!”希文看着我脸上的黑眼圈,疑惑地问道。
“哦,失眠了。”我双手捧着她的小脸,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,笑了,“真好,你一点都没变。”
“神经病。”她白了我一眼,在我脸上亲了亲,又看到了我手腕上的表,“你怎么还戴着啊,扔了吧,我看着心里有点发毛。”
我全然不在意地松开她,走进洗手间开始刷牙。
“你的电动牙刷呢?”希文看着我握着儿童牙刷刷得不亦乐乎。
“唔。”我满嘴泡沫地指指垃圾桶。
电动牙刷用多了伤牙龈,儿童牙刷柔软小巧,牙齿的犄角旮旯都能照顾到。
希文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我冲他笑了笑,她盯着我的脸,难以置信地退了一步,面无表情地上班了。
我又来到了流浪汉的铁皮屋,饶有兴趣地翻看着那些书,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天,不过瘾地带了好几本回去。走到门口,我停住脚步,又转过身去拉开抽屉,找出了一副黑框眼镜。
希文回来时,我正戴着眼镜窝在沙发中看书。我喜欢这个温暖的小家,希文未来一定会是个好老婆。
入夜,我们俩躺在床上手牵着手,希文轻声道:“发生了什么事吗?总觉得你最近怪怪的,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心脏不舒服吗?要不要去哥那儿复查一下。”
我摇摇头:“没事,一切都好,只是觉得很幸福。有你在,什么都是好的。”
她趴在我胸前,柔情万种,我搂着她柔软的身体,恍若隔世。
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,突然听到希文的尖叫声:“林宇!”
点击下方“继续阅读”看后续精彩内容。